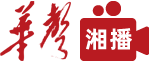龚曙光丨岳麓读书记
当真开始读点书,是到了岳麓山下。

我上师范学院那年,学校开学晚,似乎到了早秋,葱茏一派的岳麓山,竟有了星星点点红叶。校园卧在绿肥红瘦的林荫里,静寂如同山中。唯一人流涌动的地方,就是耸在小山头上的图书馆。领了借书证,头回去借书,却不知该借哪几本。卡片翻来翻去,总也犹豫不决。后来灵机一动,挑了几位看上去年纪大的同学,看看他们填什么,再把每人填的第一本记下来,凑数借了五本书。
其中有一本,便是黑格尔的《小逻辑》。回到宿舍一翻,连序言都看不懂。硬着头皮往下读,一学期只读了三分之一。同学见我老啃这本书,以为我学问了得,传出去,竟得了个读书厉害的好名声。有位外系学哲学的,约了我去操场,绕着圈子探讨辩证法。我书虽没读懂,但记忆力好,能成段成段背给他听,让他佩服得五体投地,翻来覆去逼问我:爹妈谁是哲学家?此事虽乌龙,却让我明白了一件事:若想学点西方哲学,《小逻辑》绕不过去。后来,我跑去袁家岭书店,干脆自己买了一本回来,有事无事翻一翻,直至后来一二十年。误打误撞的一本书,竟撩起了我对哲学的兴趣,以致看事论人,多多少少讲点辩证思维,不会一根筋,将自己逼进死胡同里出不来。
因了《小逻辑》,便读了黑格尔的《美学》;因了黑格尔的《美学》,便爱上了朱光潜先生的译笔,顺藤摸瓜找来他的美学著作,囫囵吞枣一起读。尽管依旧不怎么懂,但他分析具体作品的那些文字,却让我找到了一条捷径:但凡先生反复提及、重点分析的作品,便去借来读,等于得到了一份审美标准极高的书目,弥补了年少时阅读的亏欠。
我们上课时,凡遇觉得不重要,或者不好听的课,便三三两两出逃。多数同学跑去图书馆,我喜欢户外,老往岳麓山上跑。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岳麓山,山下是书院和校园,山腰是寺庙,山上,则是漫山遍野的名人墓庐。我常常跑到刘道一、蔡锷的墓地,躲着读书或发呆。那里除了清静,就是阳光特别好。那天我又往山上跑,正巧碰上了马积高先生。那时,他是中文系的主任。先生当然知道我是在翘课,却也没有批评,只说上课不听课,考试时再花更多时间复习,岂不功半事倍?老师讲一堂课,四十五分钟,只要有一两句是自己的,就算好老师,听了,就不算白听。好像读一本书,真正作者原创的观点,也就两三个,你抓住了,书就没白读。这世上,没有不值得听的课,只有不懂听课的学生;没有不值得读的书,只有不会读书的读者。再说,课是可以反过来听,书是可以反过来读的……先生和颜悦色一番话,如同一道激光,灼得我脸皮生痛,也照得我心灵洞开。此后琢磨书可反着读,愈想愈有深意。除了好些作者反话正说,藏了玄机给读者,让你反着去体味,还有思维逻辑上,顺着作者走一遍,然后逆着作者再推一遍,便有另一种思维空间。

还有一回,我去蔡锷墓庐看书,气喘吁吁爬上去,竟有一老头儿先在了,坐在石凳上晒太阳。走近一看,是王石波先生。先生那时已退休,没给我们上过课,但他的人生传奇,我早听人说过。有回先生到食堂打饭,便有人兴奋地说:那是王石波!先生早年治旧学,一派名士风度。阴差阳错让他教俄苏文学,竟也名重一时。反右时,在劫难逃被打右派,便跑去沙利文当厨师,又成了一代名西厨。再后来,选去驻沙特使馆,专门主理宴会。“文革”结束后,才被学校请回来重上讲台。过去只听说其故事,如今遇上真神,自然诚惶诚恐求教,希望先生开一份俄苏文学的书目。先生笑一笑,说:读书是件极个人的事,各人有各人的需要,各人有各人的缘分。千万别信人家的书目,名人的也别信!读书重要的,是讲缘分。碰到哪本书,是你的缘分,你的缘分构成你的知识学养体系。你照胡适的书目读,就能读成胡适?成了胡适又怎样?都说走自己的路,先读自己的书,才能走自己的路。说着指了指蔡锷的墓碑,接着又说:你看这满山躺着的人,走的是他自己的路,读的也是他自己的书。他们各读各的书,其结果,就是把自己读成了一部与众不同的书。你有缘读了这些书,比任何书目都强!也只有岳麓山,才有这些书。你能来这里,就是一份书缘……我与先生的交流,只此一次。他到底没给我开书目,却又给我开了一份大书目。我觉得,先生自己就是一本书,能碰上,就是一份弥足珍贵的书缘。
此后数十年,我果真不再找人开书目。久而久之,习惯了每年订个大概的读书计划,随心随缘慢慢读。大学期间,我最具雄心的一项读书计划,就是我行我素自己订的。我将当时学校所藏现当代散文,包括汉译域外散文,都借来翻一翻。是否真借完了,我也不确定,因为那几年,学校加速图书馆建设,藏书激增。但我所借阅过的,应在五百种左右。好些借书卡,我是第一个名字,比如张岱的《琅環文集》,周瘦鹃的《花花草草》,海涅的《哈尔茨山游记》等。当时许多同学不解:为何花这么多时间读散文?大家觉得,学中文的人,诗歌小说才是阅读的首选次选。初入大学时,我曾反复追问自己:一个汉人学汉语言文学,最大的人生功用是什么?我琢磨了许久,最后认定是交流;交流的功用是什么?是以准确、直接、生动的表达,将自己的意志与诉求,变为他人的意愿和行为。而所有文体中,最能实现这一功用的,是散文。无论说理、记事还是表达感情,散文都具备明白晓畅、直抵本质的特征。要说岳麓山下四年,我最与众不同的读书收获,就是读了这几百本散文,这几乎成了我走向未来人生的资本和底气。近年回归文学,首先选择写散文,也是因了这种积累和偏好。
十多年前换寓所,我选了河西,左岸,回了岳麓山边。虽然不是当年的校园,但属同一山脉,同一文脉。在别的河畔、山麓辗转了二十多年,再居岳麓山边,竟有一种回归老家的稔熟和亲近。寓所位居临江不远的一座小山坡,站在院子里,眺得见岳麓山顶,看得到春去秋来乍绿乍红的枫林。读书写作累了,便会驱车到山脚,沿着铺满落叶的小道爬上山,在当年读书的蔡锷墓庐,独自呆上小半天。或是读读书,或是什么也不做,只要呆在那里,便觉心宁气和,万虑俱消。

寓所装修时,我挑了空间最高最大的一间,做了自己的书房。书柜从下至上,整整五米高,几千册书摆上去,像个小型图书馆。其上最显眼的,是两套大书:一套是朋友卢仁龙做的影印版《四库全书》,一套是我参与编辑出版的《湖湘文库》。虽说这些书,我已没有勇气通读,但随时随手翻一翻,却每每有惊喜。至于那几百本朋友签名赠送的著作,读的不仅是学问和才情,更是深深浅浅的交际与友情。
如今再读书,更多是营造一种思考的氛围和状态。一本书在手,读上几页,思想便跑去了别处。到头所思所得,与作者说什么,并无多少关系。古人说开卷有益,我觉得,最大的益处,是读书可以把心收回来,让心静下来,思考一些与柴米油盐、升官发财、人情冷暖没有关系的事。至于记些金句,集些观点,甚至长些学问,已不是读书的目的。当年读书求有用,如今读书求有趣。一则另类逸闻、一段狡黠论说、一点意外感悟,都能让我会心一笑,通体舒泰。倘若还能有所触发,自己生出些感动与联想,便随手记下来,放在那里集作一本书,名曰《乱翻书》。王石波先生教诲的读书随缘,该是基本做到了。人与书凭缘分,人与思想,其实也凭缘分。有些感悟记下来,过些天再看,竟会有些惊讶,怎么自己能生出这些思想?觉得是一种莫名其妙的遭遇,一种不期而至的所得。
我读书,还有一种习惯,或许是个怪癖:读到好文章,便要动笔改。鲁迅、沈从文、汪曾祺等等,愈是名家名作,愈要逐字逐句改。这等文章,自然难得改动,间或能动一两个字、一两个句式,甚至一两个标点,便觉收获甚巨。即使一字一句动不了,也会觉得收获不小。因为这种经历多了,慢慢就能明白,如何才能把文章写得一字千钧、泰山不移。遇到好文章,看一遍不如诵一遍,背下来不如改出来。若说练写作,有时候动笔写不如动笔改。当然,这个读书写作的方法,或许也就适合我。

人说岳麓好读书,除了环境清幽,风景宜人,我觉得,重要的还是文脉与文气。吾道南来,钟于岳麓,千年薪火不绝。除了书院的学术传统,还有那些山上躺着的,都是湖湘文化血脉的代际传承人。当然,也包括山下杨树达先生那类大儒,以及后来为我传道解惑的马积高、王石波先生等。设想,若不是当年有幸遇上两位先生,我该怎么读书?又该如何做人?实在无法想象。岳麓读书的好,就在永远有一批传承湖湘文脉的人在那里,你若遇上了,便是终身之幸。再之是文气。岳麓文化积淀深厚,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化磁场,随时会校正你人生追求的指针。无论选什么职业,做什么行当,只要你看见岳麓山,想到岳麓山,便会有一种荒于读书的惶恐,疏于读书的紧迫。只要你在这个气场里,就会将读书当作成人成事、养身养心的必修之课、必练之功。这当然不是说,离了岳麓山,书就没人读,没法读,只是这世上,武有武场,文有文场,在场与不在场,差别不是小量级的。至少对我而言,罩没罩在岳麓的文气里,读书的意愿、氛围、体验和长进,当真是两种。
于抱朴庐息壤斋
2023年11月16日
(一审:蒋俊 二审:王亚奇 三审:禹振华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