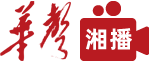父亲的腰杆
阳光燎的柏油路滚烫。下班回家,看见小区门口一位老人推着三轮车卖脱骨桃,七十多岁的年纪,白衬衣、蓝裤子,精瘦精瘦的,脸上皱纹密布,汗珠吧嗒吧嗒往下流,不知怎的,眼前就现出父亲的影子,眼眶莫名的就湿润了。
“别把摔坏的压烂了的放进去。”老人不断提醒我。
我假装没有听见,心里有了掂量,兀自挑了些卖相不怎么好的桃,老人干脆亲自上手挑了几个最饱满好看的桃儿,装袋,上秤,读数,有做惯了活的利落,也有老年人才有的迟钝。
他后背的衬衣被汗水浸出一片深色的水渍,贴着老人嶙峋的后背和突兀的脊柱,已经去世八年的父亲在我脑海中倏忽变得清晰起来。
父亲懦弱,温和。这样的性子鲜少与人红过脸。他是三十多岁时入赘到母亲家的,听母亲说,当时父亲只有一身脏兮兮的衣服,奶奶爷爷已经过世,甚至后来祖坟估计已经被别人家盖猪圈了,也难怪父亲的背前半辈子都是佝偻着的。
我的父亲大字不识几个,含辛茹苦把我们拉扯大,成家立业。他一直认为自己是成功的,在他的字典里,“成功”就是三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。他用自己瘦小的身躯全力保护和养育我们,谈不上任何丰功伟绩,可他确实尽力了。
他好像什么都没给我,又好像什么都给我了。
父亲和母亲是典型的农民,贫穷、淳朴。全家老老少少七八个,全凭父母两人劳心劳力挣来的那点工分是全然不够的。平时饭锅里就只有上面薄薄的一层米饭,下面是红薯或者藕丁。稍微厚一点的衣服都没有,用零散破布七七八八的拼凑在一起,每每寒冬来临,我们几个孩子常常冷得手脚发抖,饿得两眼发黑。
在我8岁那年,父亲为队里照管着一片红薯地。一天晚上,父亲偷偷用衣服包了一些红薯回家,第二天被发现抓到队部,头上戴一顶硕大的高帽,胸前挂一个纸牌,上面写着:“我是偷窃犯”!父亲屈着腰跪在禾场的石头台面上,原本就矮小瘦弱的身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,眼里泪水,无声无息地流。我和两个哥哥就站在旁边傻傻地看着。许是小孩子的天真,记忆中我是被造型这样滑稽的父亲逗笑了的。没有完全消化的红薯还在胃里闹腾,喉咙里像胆汁反流,是苦不死人的苦,舍不得吐掉。
我懦弱胆小的父亲,为了孩子能够吃上一顿饱饭,做了一件一辈子最出格的事。
每一个父亲都是值得炫耀的。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父亲的那一担箩筐,满足了我们童年的味蕾。为了几个食不果腹、饥肠辘辘的孩子,农闲时父亲就会挑着箩筐走街串巷去卖面,回来时箩筐里就变成了大米,和那些卷着边尽是汗水味的零零星星的角角票,偶尔
还可见到麻花、猪耳朵、打白糖等零食。每次只要老远看见父亲的影子,我们几姊妹就会一拥而上,尽管很多时候都是落空。
看见经过一天烈日炙烤的父亲,脚底起泡、全身上下像水洗过,肩膀红红地几乎要渗出血来,只是那层厚厚的老茧顽强地阻止着它们喷涌而出。我们就安安静静躲在自己的房间,不再嚷嚷着要这要那了。
我知道父亲一直是以我为傲的。中年得子,恰好赶上了改革的好时代。我也算不负他所望,成为村里第一个正经八百的大学生。在那贫瘠落后的小乡村,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。毕业后没有花费任何精力,凭教委的一张派遣单便安排了工作。工作后第二年结婚,没有当时农村结婚那么多繁琐的程序和不菲的花费,家具自办,电器都是亲戚送的,父亲就这样轻而易举完成了他一生中最神圣最伟大的责任,三个儿子都娶上了媳妇,没有一个单身。为这个大大的成功,父亲至少念叨和炫耀了不下一百次。
2004年,我攒8万元买了一辆别克赛欧车,开回老家时,父亲站在村口高兴得逢人就说我儿子开上了几十万的豪车,当时羞得我只想往地底下钻。父亲一辈子没见过多少钱,根本不知道几万和几十万之间有多大差距。
作为医生,我当然也乐意为父老乡亲做点事,乡亲们三病两痛,都喜欢咨询我,在我们医院来住院,我也是尽能力行方便。加上老爹喜欢“炫耀”,村里两位哥哥推波助澜,在老家我也慢慢有了点“名声”。因为虚名在外,村里打水泥路安路灯等公益设施,我自然是跑不掉的,每次都打肿脸充胖子拿自己微簿的工资捐一些钱,村支两委领导也就经常提点东西上门慰劳老爹,每次都喝得酩酊大醉,满嘴跑火车,常年佝偻的腰此时挺得笔直。我也顺坡下驴呵呵苦笑,为村里作了些贡献,也满足了父亲晚年的虚荣心,这些捐赠也算价有所值。
这就是我的父亲,勤劳、善良、懦弱、平庸,我们之间有说也说不完的故事。
父爱,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温柔守护,亘古绵长,厚重深沉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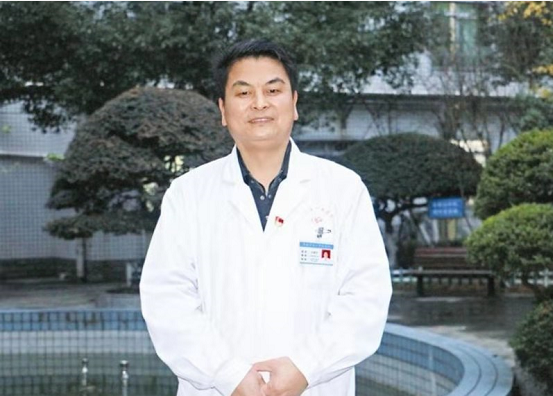
作者简介:
王腊忠 湖南常德市第一中医院口腔科主任、主任医师,湖南中医药大学硕士生导师、湖南文理学院客座教授、常德散文家协会党支部书记、《散文时代》副主编、“桃源诗刊社”副社长、《桃源诗刊》副总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