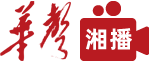传承力量 | 冲进核爆现场提取标本的父亲
刘文彦
父亲(1931~1993)是湖南益阳市西流湾人。很久以前,西流湾就是旧时解甲归田将士、安化沿资江而下放排工的混居之地,这个地方民风彪悍,父亲身上有先人影子,所不同的是,他是全家唯一读过书的人。
父亲从小就表现出很强的独立思考能力,很聪慧,从小学到中学功课都很好,湖南和平解放后,父亲当选益阳市一中学生会主席,那时校园积极向上氛围很浓,无论是课后校内木工、制造粉笔等手工劳作实习,还是出刊校园进步宣传栏、组织学校排球比赛,父亲都是主角。父亲的毛笔字漂亮,逢年过节时,西流湾的邻里们都请父亲写对联。父亲的排球打得好,他打二传手位置。父亲身体很壮实,曾在放学路过马路时,被卡车从大腿碾过,他没事,一跃而起,在路人惊诧眼神目送下回家了。我怀疑父亲有没有痛神经,从来没有见过他喊痛,既便临终前身体疼痛难忍,他都不哼一声。
父亲高中毕业就报名参军了。奶奶说,他们那群学生是坐轮船走的。我父亲特意坐在最船尾,盘着双腿,笑嘻嘻的使劲地向奶奶招手,奶奶挤在欢送的人群里,不住地擦着眼泪,想扯起嗓子交待几句,却哽咽得发不出声音。
到了部队后,因父亲的高中文化水平在部队算得上是宝贵“秀才”,他去朝鲜参战的几次申请都没有被批准,而是被留在了郑州市炮校当军事教员培养。
父亲融入军营快。原长沙炮校政委、父亲的老战友曾对我说,“他在我们这群人中很出色,精力很旺盛,大家几天野外拉练下来腰酸背痛的,他却一个人使劲地擦炮筒,把炮筒里里外外擦得亮铮铮的,这可是力气活儿,更是细心活儿呢......他脑袋瓜子好使,肯钻,肯学,他的文化修养不会比一般人低,他看的书很多,很杂,古今中外的都有,每本书上都密密麻麻地写满了读书笔记,那钢笔字很棒,看上去很稳,很有力道,入伍一年后就入党了,被提拔为区队长,他带兵行,会做政治工作”。

父亲当区队长时,队里就有很多四二年参加八路的兵,资格比他老得多,可这群老兵喜欢我父亲。因为,每天的军训操场上,他们总能看到我父亲摸爬滚打的身影,我父亲的军事素质很过硬。父亲关心战士,从不当众训斥人,即使战士捅了搂子,他也只是个别叫到办公室批评一下,事后将责任一人扛了。队里有个家境很困难的战士,我父亲多次暗地里以战士的名义给他家里寄钱,寄物,战士们打心眼里敬他,服他。
我听父亲说过一件事,那年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来炮校视察,炮校举行阅兵式,整个方队走不齐。检阅台上,许光达司令员皱着眉头。许司令员的严厉是出了名的。他每次视察部队,总是戴上白手套去摸摸枪口和炮筒,一旦发现手套黑呼呼的,就要严厉训人的……炮校领导急调我父亲指挥阅兵方队。父亲很快控制了队伍节奏。当一队队方阵、一辆辆炮车整整齐齐地从司令员眼前开过时,司令员庄严地行着注目礼。事后,据悉司令员对我父亲很满意。
思想过得硬,军事过得硬,作风过得硬,使父亲得到了组织上高度信任,并先后委以两次极为保密的光荣任务,一次是“炮击金门”,一次是参加我国第一次原子弹试验。父亲不辱使命,他用生命诠释了中国军人的那份信仰、忠诚、无畏、担当,他作为军队先进分子受到了毛主席的接见。
父亲参加第一次原子弹试验时,负责原子弹爆炸后提取核爆中心区域标本。他和他的战友们勇敢地冲进核试验区采集实验标本,遭到了严重核辐射杀伤,父亲七窍流血,被抬到解放军鸡公山医院,昏迷不醒多日。
奶奶生前说过“只知道你爸爸因公出事了,家里来了好多领导,家里人哭哭啼啼地准备后事了,哪知你爸爸没有死,这天他回家了”。

母亲说,父亲求生愿望强,从昏迷中醒来了。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家里人,醒来的第一件事,就是回家报平安。他是在两个护士撑扶下,拖着沉重的身躯,气喘吁吁的一步一步地爬上三楼,出现在家人面前,直说“我没事我没事”。返回医院后,为了重新归队,父亲以顽强的毅力克服药物产生的严重呕吐反应,尽量进食,增加营养,吃了就呕,呕了继续吃,终于度过了生命危险期。
我经常感慨,我们与父亲拼命干的那个年代所面对的艰难和挑战简直没法比,父亲那一代人的精神十分可贵。算一算父亲已经离开我们28年了,只要谈到父亲,我眼前就出现他昏迷不醒被抬进鸡公山军医院的场景......
生如夏花之绚烂,死如秋叶之静美。
如今缅怀这些勇敢地冲进核爆中心区域采集实验标本的父辈,我心中充满崇敬,他们都是“林俊德”。
父亲因伤病于1971年2月回家乡休养。从此,他结束了长达20年的军旅生涯。
父亲是一个有家国情怀的人,而且很睿智,从小就有报国之心,生前他曾笑着说“小时候常双手反剪,独自面对一江之水遐想”。从部队下来后,他很清楚,伤病缠身使自己从军报国理想中道而止了,但他不会放弃,他乐见自己的抱负在日常生活中开花,在妻子儿女身上得以实现,这种大爱之念让他的离休生活过得很充实,身心愉悦,一定程度地延长了他的生命。如欣然接受邀请去中小学做传统报告,讲得激动时放歌一首《志愿军战歌》,如为周边村民调解民事纠纷,当事人双方都要找刘嗲(村民对我父亲的尊称)评评理,问题解决后,大家都开心,父亲更是如此,他那精神头给人感觉他不像一个病人,又如父亲在家的附近废弃土地一角开辟一块菜园子,戴着草帽扛着锄头松土、施肥、下种、浇水,忙得不亦乐乎,皮肤晒得黑黑的,还时不时去附近竹山转一圈,看有没有竹笋挖,每天下午边头手上总会带一把地里的新鲜菜回家,见人就笑呵呵地打招呼,他很像附近和善的农民伯伯。
父亲对子女很是寄予希望的,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,要求我们学好数理化。在我们三兄妹学习上,父亲在我身上花的精力最多。
我是77届高中毕业生,我们这届学生没有系统学习过,整天学工学农,能够发动柴油机就算物理课考试过关了。77年高中毕业后,我就上山下乡了,当年秋天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,面对高考试题,我们无从下笔。为了我们这些知青前途和出路,78年知青点领导给我们联系了一所师资力量很强的中学,让我们脱产插班复读,吃住在学校。学校伙食缺油少肉,总觉得没吃饱。这段复读期间,父亲经常给我带来干炒面及卤肉,干炒面用开水一冲,就着卤肉随时可以吃,香香的。父亲每次来学校,总忘不了去拜访任课老师,了解我的学习情况,有时还像老朋友一样,和数学老师探讨平面几何难题。我读大学后,他还是这样的,经常来看我,每次来看我,都要给他的老战友们打电话,“我在长沙,我在我儿子学校里呢”,语调里明显有了“自豪”意味。
虽然我不认同父辈安排孩子们的人生道路,但在资助我求学、力主我从事金融工作问题上,我要感谢父亲,事实证明他是对的,求学使我的逻辑思维能力和写作能力得以提高,从事金融工作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,提升了我对国家经济政策的领悟能力,拓展了我的社会瞭望视野,这些都为我走上参政议政之路打下了坚实基础。也是在这个过程中,我能感觉我在圆父亲未竟的报国之心愿。比如,每次书写社情民意时,父亲认真、严格的做事形象总会在我脑海里萦绕......
我读大学那几年,感觉父亲身体状况一年不如一年,感觉父亲老了。
大三那年的一天下午,有同学叫我,说父亲来看我了,就在教室外面。我出去一看,父亲提着一袋好吃的站在走廊上,朝我微笑,我发现父亲穿了40年的军装摘掉了帽徽和领章,我能从父亲微笑中捕捉到那份痛苦,父亲说他的肝病到了失代偿期。我当时很难受,我低着头,不想让父亲看到我在流泪。他对病情的恶化趋势早就有了思想准备,最主要是上交了军装上的帽徽和领章,让父亲痛苦,军装就是他的生命。
其实,父亲完全可以对自己好一点,但他情愿自己忍着、憋着,也不愿意给国家和军队添麻烦。如最初回地方养病,组织上给他颁发一本带有“医疗绿色通道”性质的《伤残军人证》,被他退回去了。又如,八十年代中期,部队要父亲归队,帮助组建长沙炮校,被他谢绝了,他说身体不好,不愿意拖累部队。
好在我母亲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,让父亲过了一点好日子。我父母感情很深。

父母是自由恋爱的,他们性格互补,父亲是军中教官,沉稳、内敛,母亲是教师,却性格外向、刚烈。母亲习惯下班回家后,在父亲面前滔滔不绝地谈工作,父亲一般只是倾听,末了,很从容地谈了一点自己的想法,话不多,但显然是深思熟虑过了。
每逢周末,人们经常能看到母亲和父亲一同去种菜,一同去散步的画面。
我母亲是一位很优秀的知识女性,是哲学教授,是全国教育系统劳模,当过中学校长。但从某种角度说,母亲成功的背后,有父亲的巨大影子。父亲经常向母亲口授处理各种工作难题方法,帮母亲出谋划策,甚至帮母亲进行整体规划,并细化到整体实施举措和阶段性步骤,每每都能取得良好效果,母亲高兴得直鼓掌,父亲的表情很舒服。
我在县一中读高一那年的一天,教育局局长在路上遇到我父亲,他对我父亲说,“老刘,你干脆来我这里,我当局长,你当副局长帮我”。虽说是一句玩笑话,也是业内人士对父亲能力的赞赏。

1993年元月20日,大寒,是父亲最难熬的日子,他的生命进入了倒计时。
我母亲坐在父亲的床边,她怎么也不相信我父亲会走的。我父亲对我妈笑了笑说,我没事,一定会战胜病魔的。
我知道,父亲是在宽我母亲的心。
上午10时,我母亲从我父亲恋恋不舍的眼神里,似乎察觉到了一些不妙,但她还没有完全做好思想准备。我看到父亲艰难地伸出一只手,抚摸着妻子的脸,又笑了笑。我母亲还没回过神来,父亲就在我母亲怀里永远地闭上了眼睛……
父亲在我心里很高大,是标杆。
如今,我退休了,有时间了,我很想去打听、探望父亲的战友们或战友子女们,如果能见到父亲的老战友、战友子女,同他们交谈,我相信能获悉有关父亲的更多信息。如此,我就离父亲更近了。
作者: 湖南省人民检察院监督员 湖南省文史研究馆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