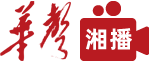豆子茶何来
凡事皆有两面性,饮茶也不例外。“释滞消壅,一日之利暂佳;瘠气侵精,终身之害斯大”。在茶成为日常饮品的漫长过程中,先民们充分体会到了茶的功效,同时,又逐渐认识到了茶的副作用,并摸索出如何消解的方法。《茶经》云:“茶之为用,味至寒。”现代科学已经找到了“味至寒”的原因——茶叶中含有的咖啡碱和茶多酚导致“呕酸寒胃,令人失睡”。然而,在古代,人们缺乏科学的方法和手段,只能根据经验的积累来进行归纳总结,寻找合适的平衡之道。杂果烹茶,即在烹茶时加入各种各样的辅料,能显著地降低茶的刺激性,就是先民们长期经验所得。一般来说,添加何种辅料往往有中医药理论作为支撑。
上一篇文章豆子茶曾经说到,唐宋文人几乎普遍对杂果烹茶表示不屑,讥之为“沟渠弃水”。豪放如东坡先生者,则坚决反对烹茶用姜盐,“近世有用此二物者,辄大笑之”。然而也有例外。北宋大文豪、苏门四绝之一的黄庭坚爱茶懂茶,作过许多茶诗,还写了一篇《煎茶赋》。下面这段专门谈到了他亲手杂果烹茶破解茶寒之法,有理论有实操,非常精彩:
或者又曰:寒中瘠气,莫甚于茶。或济之盐,勾贼破家,滑窍走水,又况鸡苏之与胡麻。涪翁于是酌岐雷之醪醴,参伊圣之汤液,斮附子如博投,以熬葛仙之垩。去藙而用盐,去桔而用姜,不夺茗味,而佐以草石之良,所以固太仓而坚作强。于是有胡桃松实、庵摩鸭脚,勃贺靡芜,水苏甘菊,既加臭味,亦厚宾客。前四后四,各用其一,少则美,多则恶,发挥其精神,又益于咀嚼。
惟用典偏且多,词语生僻,不易理解。大意是:茶伤脾胃,损元气,故在茶水中添加盐、鸡苏和胡麻同饮,希图尽快排出体外。而这又有赖于肾脏的代谢,致肾脏负担较重,所以防止寒中、瘠气必须从固胃(太仓)强肾(作强)着手。参照上古名医调理饮食的方法,用剁成骰子大小的附子熬水,并且加入白垩调剂水性,再辅以姜和盐。在以上四物的基础上,再从另外四种果实(鸭脚为白果的别称)和四种植物(香草)中各选一种搭配,增加香味,丰富口感。通过此番操作,可以改良茶性,从而达到“固太仓而坚作强”之目的。
既煎茶,茶为君,不夺其味,这是根本。后世形形色色的杂果茶,须以得茶味为要,否则必沦为争奇斗怪之举。附子、白垩为臣,姜、盐等为佐使,一碗茶汤中君臣佐使都齐全了。虽为治茶,却是医家的方术。苏东坡《寄周安孺茶》:“姜盐拌白土,稍稍从吾蜀”,可见白垩是蜀地民间煎茶早有的丹方,现在弄明白了其作用机理是中和胃酸。附子乃大热之物,有回阳助肾之效。又“附子无姜不热”,用姜能激发附子的热性并降低其毒性,亦见配伍之妙。这样“固太仓(胃)而坚作强(肾)”的措施俱备,其余东西只有调剂口味的作用,当然不能也不需要每样都加。“少则美,多则恶”,多了夺茶味,兴味索然,毕竟是煎茶而不是熬药。
黄庭坚这篇《煎茶赋》,作于被贬戎州(今四川宜宾)期间,与其堂弟黄叔向煎茶论茗之夜。作为朝廷官员,他有机会喝到当时的三大名茶,即福建建溪茶(龙团凤饼)、江西双井(黄的家乡)茶和浙江日铸茶。在蜀地的贬谪生涯,又品尝到了自古以来盛产茶叶的川渝地区的各种佳茗。茶文化发展到北宋晚期,已经有了品牌意识,各种茶书和诗赋中有许多这方面的记载。从行文分析,三大品牌茶已深入人心,对人的副作用较小,但价格昂贵,不是大众消费得起的。其他的茶有六种可入他的法眼,也应该是不俗之物。即便如此,还是存在“呕酸寒胃,令人失睡”的麻烦,遑论民间普遍饮用的粗制草茶。这个问题即使到现在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,很多人喝绿茶容易引起肠胃不适。唐宋时期民间散茶,其刺激性远较现代茶为烈。因此,黄庭坚从医理和文化的角度出发,对杂果煮茶之类的功用和原理,进行了一番阐述。此文对我们了解杂果煮茶这一习俗的渊源和演化有莫大的帮助。
民间的喜好并没有也不会因为文人的轻视而消亡,相反愈来愈盛。到了明代晚期,煎茶所添之物越来越丰富,遂成时尚,当时话本小说、文人笔记等多有记载。如《金瓶梅》所记西门府上名目繁多的烹茶果物,一方面反映了晚明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面目,以及巨富之家显摆斗阔,奢靡虚荣之风气,也不排除作者借物讽人,嗤笑西门庆潘金莲之流贪得无厌,无所不取的本性。因为其中一些添加物过于奇葩,匪夷所思,完全超出了对饮茶的认知与想象:
“火边茶烹玉蕊,……点了盏浓艳艳(酽酽)芝麻、盐笋、栗丝、瓜仁、核桃仁、夹春不老、海青、拿天鹅、木樨、玫瑰泼卤六安雀舌芽茶”。
这些奇奇怪怪、闻所未闻的东西粲入茶中(有人考证出“春不老”为腌雪里蕻),在今人看来,无疑是糟蹋了那一盏六安雀舌芽茶。或许,那时的人,或者在那样的环境下,杂果煮茶的目的并不为了茶,也不在意夺不夺茶味,就像现代人追捧奶茶一样。
把手机拿稳了,光看名字,还有更雷人的土豆泡茶、芫荽泡茶:
胡桃松子泡茶、福仁泡茶、果仁泡茶、蜜饯金橙子泡茶、盐笋芝麻木樨泡茶、梅桂泼卤瓜仁泡茶、瓜仁栗丝盐笋芝麻玫瑰香茶、熏豆子茶、姜茶、榛松泡茶、木樨青豆泡茶、土豆泡茶、芫荽芝麻茶……
不过此土豆非彼土豆,应指某种地产豆子,并非马铃薯。因后者引入中国的时间大约在17世纪,而《金瓶梅》成书在16世纪隆庆到万历朝时期。芫荽当指芫荽籽,《本草纲目》称“芫荽性味辛温香窜,内通心脾,外达四肢”。说来还是旧瓶装新酒,走的温热克寒的老路子。有作者把土豆、芫荽当成菜蔬入茶,大呼小叫,显然未做考究,犯了望文生义之忌。但明代煎茶选用菜蔬,也并非空穴来风,顾元庆《茶谱》专列“择果”一条,其中就有好几样菜蔬:
茶有真香,有佳味,有正色,烹点之际不宜以珍果香草杂之。夺其香者,松子、柑橙、杏仁、莲心、木香、梅花、茉莉、蔷薇、木樨之类是也。夺其味者,牛乳、番桃、荔枝、圆眼、水梨、枇杷之类是也。凡饮佳茶,去果方觉清绝,杂之则无辨矣。若必曰所宜,核桃、榛子、瓜仁、枣仁、菱米、榄仁、栗子、鸡头、银杏、山药、笋干、芝麻、蒌蒿、莴苣、芹菜之类,精制或可用也。
“……蒌蒿、莴苣、芹菜之类,精制或可用也。”以“精制”论,亦非新鲜蔬菜可用。顾元庆是明中叶苏州人氏,所见所闻或多为吴地习俗。芹菜入茶,似乎传承到了二十世纪前后。清末民初南京人潘宗鼎所著《金陵岁时记》,被认为是记载、研究南京风俗的开山之作,其中就描述了南京这一旧俗:
“盐渍白芹菜,杂以松子仁、胡桃仁、荸荠,点茶,谓之茶泡。客至则与欢喜团及果盒同献。”
总之,明代书籍里状绘的林林总总的茶果中,姜、盐(或盐渍果蔬)、豆子和芝麻均位列其中。相较于唐宋时期烹茶,豆子似乎是明代新增的。《金瓶梅》中提到的熏豆子茶,是否和后世流行于苏州湖州地区的熏豆茶一样不得而知。详细记载湖南豆子茶的文字,目前所知最早见于《清稗类钞》。《清稗类钞》为清末杭州人徐珂所著,对研究清代社会经济、下层社会、民情风俗有较高的参考价值。录入该书之《饮食类》卷的姜盐豆子芝麻茶,与现今流行于民间的完全相同:
茗饮时食盐姜莱菔/长沙茶肆,凡饮茶者既入座,茶博士即以小碟置盐姜、莱菔各一二片以饷客。客于茶赀之外,必别有所酬。又有以盐姜、豆子、芝麻置于中者,曰芝麻豆子茶。
长沙人食茶/湘人于茶,不惟饮其汁,辄并茶叶而咀嚼之。人家有客至,必烹茶,若就壶斟之以奉客,为不敬。客去,启茶碗之盖,中无所有,盖茶叶已入腹矣。
走进当年长沙城的茶肆,茶博士沏的一壶芝麻豆子茶,清香袅袅,余味不散。现在长沙县、望城区民间仍有此茶俗,盛行不衰的汨罗和湘阴,千余年一县,于1966年分治,此前一直隶属长沙府,因而这一习俗也完全是老长沙的旧俗。
既然茶伤脾胃,为何独湘人咀嚼吃茶?难道说湘人有特殊的胃肠功能,能消解茶之副作用?这奥秘除了姜盐的功效,主要还在于茶叶。煎茶用的茶叶,一般采用烟茶。烟茶制作工艺,最大的特点在于杀青迥异于世。不同于晒青和炒青,烟茶用烧开的水烫(泡)青,即将采摘挑选的鲜叶汆入开水中,讲究快进快出。慢则茶烂如泥,无法进一步制作,过快则杀青不足,此环节极考验制茶人功力。待茶叶摊开散热将冷未冷之时,反复揉捻搓制,此时青汁滲出,咖啡碱大量流失。至条索匀净,慢火烘干即成,因略携烟味,俗称烟茶。如此制成的茶,茶性相当温和,再辅以姜抵消寒气,自然可吞食入腹。
烟茶茶性冲和清淡。平凡的本色,却是豆子茶的灵魂。倘若改用他茶,即便贵如龙井碧螺春,也差之千里,难得其真味。豆最佳选择是大豆即黄豆,香气正,口感佳,他豆不足论。现今有用红皮花生米替代豆子的做法,但花生香味浓烈,侵夺茶味,亦不可取。姜盐豆子芝麻茶组合中,哪样都可以缺,唯独茶必不可少,否则便与饮茶无关,那真是喝汤了。
纵观茶的发展历程,饮茶方式从繁到简、由难到易--不论茶礼茶器茶俗,还是茶之内容,都经历了简单、复杂再回归简单的过程。这其中,制茶工艺的不断改进起到了关键作用。明初散茶流行后,总体趋势是更注重体验茶之自身的韵味和魅力。到了清代,冲泡绿茶更加普遍,煎茶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,这从成书于清初的《红楼梦》中可见端倪。即便是杂果煮茶,所杂之物也趋于简单、搭配固定,且都以居家平常之物为主,豆子茶便是最好的例证。完全可以推断,豆子茶无疑是古代花样繁多的杂果茶的简配版,是历史悠久的传统饮茶方式的活化石,值得我们品饮与珍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