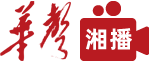郝安专栏|霜降赏读:霜叶红于二月花

九月中,太阳到达黄经210度。是时冬令未至,气肃始凝,而寒霜先降。
霜降是秋季的最后一个节气,意味着秋天行将结束;这时候气候渐寒,露结为霜,是一年中有霜期的开始,宜人秋季渐次向岁暮冬季过渡。
其实露霜皆由地发,不是从天上降下来的。故节气霜降不能从字面理解为降霜,气象学也没有“霜降”的概念。霜降表现的是气温骤降、温差变大的气候特征。
自兹以降。盖降者,还取到来的意思,描述的是寒霜的驾临,带来了凛冬的信号。山明水净夜来霜,数树深红出浅黄。暮色苍茫中,一天天陡坡式的气温变化,让蜂蝶无踪,令蛰虫无声,大地复又归于安谧宁静——
头候豺乃祭兽。豺狼加紧捕捉猎物,并将储备过冬的口粮陈列显摆,接着仰天嚎叫几声,烘托出感恩报本,容忍它对弱小兽类捕杀的祭祀仪式感。
次候草木荒落。西风漫卷,其气凛冽,其意萧条。几番风刀霜剑的摧残磨砺,树木变黄,树叶飘落。霜降百草枯,纷纷零落之秋叶给生命以静美收尾。
末候蛰虫咸伏。喧闹的秋虫悄悄离场,懒洋洋缩进洞中,耷拉眼皮垂下头来,蜷着身子不动不食,以低耗能的麻痹状态让生命冷藏,一觉能睡到明年。
走过春的生机、夏的热烈、秋的收获,大轴霜降节令,是阳气由收到藏的过渡。浓浓的凛若寒霜,渲染出晚秋的绚烂多彩,赋予大自然一份成熟、深沉的美。
正是霜降这最后的一幕献演,为即将告退的秋天划出了一道绝美休止符。与之比肩媲美、相得益彰的,是在季春清明时节杏花问酒,又在季秋霜降节令登高访山的杜牧《山行》——
远上寒山石径斜,白云生处有人家。
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。
弯弯曲曲绵长蜿蜒的石径山路,隐隐约约山石砌就的几户人家,缭缭绕绕升腾漂浮的雾气白云,密密匝匝经霜漂染的枫林红叶。明明写的全是景,但又全是情的宣泄,意境幽美、意味无穷,充满生机和情趣。构成了一幅诗中有画、画中有诗,意中有景、景中有意,不是春光、胜似春光的山林晚秋图。

晚唐杜牧人称小杜,以别盛唐杜甫。究其为官为文、做事做人,小杜迥异于一般舞文弄墨的骚客,显得大气磅礴,大有见地,堪称大家。他论政谈兵,最早认识到枪杆子和政权的关系,说“信知国家者,兵为最大”,与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的毛公石破天惊提出的“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”著名论断,高度契合。
樊川居士天资横溢,恃才傲物,不拘小节,不屑逢迎,即便官场失意失败,也并不介怀,没有叹老嗟贫。著文作诗,力矫时弊,更如铜丸走坂,骏马注坡,有太白之风。就对体裁的掌握而言,七言绝句一体,殆尤专长。状写秋山景物的《山行》,就表现出他在起伏跌宕中能一气呵成的妙笔功力。
岁往月来,忽复重阳霜降。不妨擎一把茱萸叶,挎一壶菊花酒,系紧鞋带,跟随情致豪迈的杜兄一道,吟着《山行》去山行吧。
首句从遥望处落墨,说寒山,道石径,直接点题。不过,这铺上石块弯弯斜斜的山路,恰如这平平淡淡的诗句平平缓缓,不高不峻,也不险恶。
次句说山的深处生起白云,白云生处住有人家。表明寒山特指秋天的山,而非荒山。山上有车马行驶的路,有人来往,又有住家,这山便有了人气生意。
跟上句一样,这句描写是任谁都一目了然能看到的景色,很自然,很普通,虽也很顺溜,但实在看不出有什么独特或出色之处。
原来,绝句之法,讲究起承转合,婉曲回环;其出奇出意,句绝而意不绝,变化工夫全在第三句。让我们拭目以待。
继续走,接着吟。第三句一经出口,感觉是有些不一样了。傍晚山行,本来是要“远上”赶路的,现在流连忘返,不但“停车”,还要“坐爱”了。设的悬念回应是“枫林晚”:眼前一幕夕阳斜照、红霞如火,万山红遍、层林尽染的景致,实在让人不忍不舍,挪不动脚步。
既简练、又丰满的第三句,处在事物经过开始、发展后,到了变化这一重要阶段,离结束只一步之遥了。前面一步一行,一行一句,至此虽然让人怦然心动,但也还只是叙述山行的过程,和一二句一样,总体给人的感觉还是一般般。
且行且吟,不急不慌。果然,末句“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如晴空里一道闪电、平地上一声炸雷,又或沙漠里仰卧的一汪清泉、草地上缓缓移动的一群白羊,让人心头忽地一喜,眼前蓦然一亮,身子不由一颤。
七个字,出人意料;真名句,出奇制胜。霜叶胜花,道常人所不易道出者,一经诗人紫薇道出,便留传千口。这是全诗的中心,胜败的关键,是欲擒故纵、欲扬先抑,浓墨重彩、凝笔聚力抒发出来的。到这个时候,有了魂为之夺这一句,整首诗便意态飞动,富有理趣,境界全出。

秋枫春花,各美其美。杜公不惜先以平顺笔调状写山行景物;一俟铺平垫稳,蓄势已足,便笔锋忽转,让秋景和春光争艳,强调霜叶胜过春花,一举扭转乾坤,也让诗坛渐趋萎靡的晚唐,闪现出一缕返照的回光。
一个难字也没有,一个典故也不用。曾经的小学生、现在的小学生几乎都是张口就来。但有两字,一是字音上的,即“斜”到底读什么;一个是字义上的,即是“生处”还是“深处”,却引发了千年之争。其实“斜”的两音都说得通。从诗韵搭配来看,与上下句实现押韵的读音,更富音律节奏美。生是动词,生机勃勃,更具神韵,更现动感,无疑要高妙许多。
秋去秋来,人至人往。从满目金黄到满目枯黄,目送的是一个季节的流逝,迎来的是又一段生命的成长。身躯倦,且将养;鬓微霜,又何妨。今夜纵然霜露重,明早又是太阳红——
挥手别秋从兹去。在百兽都开始预备储粮的时节,人类也该遵从大自然的指示,将曾经放下,让往事随风,安然、坦然、泰然迎接冬天的到来了。
(一审:邓望军 二审:石伟 三审:禹振华)